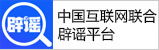李慰农年轻时的照片。

位于青岛的李慰农烈士雕像。(资料图片)
李慰农,一位从巢湖边走出的革命烈士,合肥早期共产党员之一,他用鲜血谱写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赞歌。而他与邱以珍的爱情,因“平等、信念、等待、牺牲”而感人至深,他们把家的温暖升华为国的担当。
油菜花下的平等之爱
巢北油坊郑村的春天是被金黄色的油菜花托起来的。李慰农故居前的那片油菜地,该是全村最早醒的。晨露还凝在花瓣上时,就有村民扛着锄头经过,脚步轻得怕碰落了花。
李慰农原名李尔珍,1895年出生于巢湖一个普通农家。小时候,李尔珍背着布书包从县立中学回家,脚步会在油菜地边慢下来。他蹲在田埂上,看蚂蟥爬过湿润的泥土,看蝴蝶停在花盘上,耳边是乡亲们扛着犁耙走过的吆喝,是母亲在堂屋唤他吃饭的情景,他在作文里写“油菜花开时,农人之苦亦深”,笔尖落的是眼前这片花下的土地,是乡亲们“终岁劳作,不得一饱”的愁容,可这片油菜花,已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——要让这金黄不只开在春天,更开在乡亲们的饭碗里。
1912年的巢湖岸边,柘皋镇北桴槎山清水涧油坊郑村周边的金黄色的油菜花漫过田埂时,李尔珍早已踩着晨露从巢县县立中学步行回家。推开柴门,母亲攥着他的手往堂屋引,帘布一掀,穿靛蓝布衫的姑娘垂着头站在八仙桌旁,辫梢系着朵新摘的栀子花——是邻村的邱家女,母亲说:“她是你的媳妇。”
那时他还没叫李慰农,满脑子是谭嗣同的《仁学》,是“冲决网罗”的呐喊,可看着邱姑娘局促地把衣角攥出褶皱,终究没说出口反对的话。新婚夜,他笨拙地递过一盏煤油灯:“我给你取个名字吧,叫以珍,邱以珍,珍贵的珍。”姑娘抬头时,眼里亮得像落了星子。
婚后的日子,是书声与纺车声的和鸣。他在油灯下备课,写“农业救国”的札记,邱以珍就坐在对面纺线,棉线穿过锭子的沙沙声,成了他夜里最安稳的背景音。农忙时,他帮着下地,她总把掺了米的粥碗或者油炒饭先推给他:“你读书费脑子,多吃点。”有次他教学生读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回头见她站在教室外,抱着刚织好的白纱布,眼里满是敬慕。
36封家书背后的守望
中学毕业后,李尔珍考入安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,立志攻读农业科学,并从此改名李慰农。每次回家,邱以珍都提前在村口等,包袱里总裹着炒花生和缝好的布鞋。他给她讲城里的事,讲火车怎么跑,讲要让农民都有饭吃,她听不懂大道理,只笑着点头:“你做的都是正事,我等着。”女儿出生那年,他在油灯下抱着襁褓,轻声说:“等将来,让她也读书,不做睁眼瞎。”邱以珍摸着他的手,指腹上有握笔磨出的茧,她把自己的手覆上去:“家里有我,你放心。”
1919年秋,李慰农拿到赴法勤工俭学的录取通知书,整夜没合眼。邱以珍看他辗转,默默把新絮的棉袄叠进包袱,又把攒下的银元塞在他贴身的衣袋里。送他去码头那天,她抱着儿子,女儿拽着他的衣角哭,他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,又看向邱以珍:“以珍,等我回来,咱们的日子会不一样的。”她忍着泪点头,直到船影淡出视线,才敢用袖口擦干湿润了的眼睛。
他在法国的5年,寄回36封家书。信里写巴黎的铁塔,写和周恩来、赵世炎讨论革命,也写“夜里常想起你纺线的声音”。邱以珍把信读给公婆听,读一遍就折好放进木匣,匣底压着他临走时穿的蓝布衫。有次儿子问:“爹什么时候回来?”她指着天上的月亮:“等月亮圆了又圆,爹就回来了。”
烽火里的长别与坚守
1925年,李慰农归国赴山东工作,船经上海时,离巢湖不过百里。同志劝他回家看看,他望着长江水,想起邱以珍的笑容,终究摇了摇头:“国不安,家何安?”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家乡那么近。
5月,李慰农到青岛领导党的工作、开展革命斗争。7月26日,李慰农在去小鲍岛召开秘密会议时被反动军警逮捕。敌人逼他说出在青岛的“同党”,李慰农坦然地说:“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!”29日,李慰农在青岛团岛海滨的沙滩上被反动军警秘密杀害,时年30岁。
青岛团岛的枪声响起时,邱以珍正在巢县老家油坊郑村的土坯房里缝新鞋。她不知道,那个答应“等日子好起来”的人,再也回不来了。后来噩耗传来,她抱着那36封家书坐在门槛上,从日出到日落,没哭出一声。倒是年迈的婆婆,天天坐在村口朝北望,直到双目失明,还在念叨:“尔珍该回来了,以珍还等着他呢。”
许多年后,有人在整理李慰农的遗物时,发现一张泛黄的纸,上面是他赴法前写的字,字迹里藏着温柔:“以珍如晤,此去万里,非为功名,实为家国。待河山澄清日,必归巢湖,与君共话桑麻。”只是这诺言,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,唯有巢湖的水,年复一年地流,带着这段藏在烽火里的爱情,静静诉说着一个男人对家国的忠诚和对妻子的深情。(杨玉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