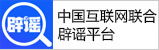90多岁的阚璞在为年轻一代讲述革命故事。

阚璞在新四军军部旧址前留影。

年轻时的阚璞。
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,她虽未持枪冲锋陷阵,但却在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场上,守护根据地的经济命脉。她是阚璞,一位在“钞票”上抗战的女战士,用青春与智慧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。
一、浮槎山下初长成革命路上觅知音
1926年1月,阚璞出生于今天肥东县石塘镇一个叫阚中份的小村里。阚家世世代代是农民,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,精耕细作祖上留下的十几亩薄田,倒也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只是随着阚璞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和她的相继出生,家里人口增多了,生活便越发困难了,以至于阚璞生下来后就没有大名,因为她在兄弟姐妹中最小,大家就喊她“小老巴子”。
屋漏偏逢连阴雨。阚璞一岁多时,母亲便因病去世了。考虑孩子太小,父亲忍痛将她抱给人家养。没想不久后阚璞生了一身疮并引起感染,那家人也不愿收养了。姐姐只好又将她接回了家。
据阚璞后来回忆说,虽然一家人的日子更艰苦了,但阚中份村位于风景秀丽的浮槎山下,她从小便像男孩一样喜欢爬到山上玩,倒也无忧无虑,更锻炼了她胆大心细、不畏艰险的性格。这为她后来参加新四军、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。
五岁那年,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,阚璞和邻村一名男孩定了“娃娃亲”,双方家长商定待两人成年后便可完婚。“1943年,我17岁了,得悉我未婚夫几年前就参加新四军了,就在定远县藕塘镇。于是我的两个哥哥带着我,假装成布贩子,一起赶往藕塘寻找我的未婚夫。”阚璞在回忆文字中说。
到了藕塘镇,阚璞他们很快找到了未婚夫李济生,并且知道了他在新四军二师工作。经他介绍,阚璞也参加了新四军。不久后,他们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了。“那时结婚可简单了,我们买些花生、瓜子、枣子,放在桌上,大家围坐一起,说说笑笑,就算办个仪式了。”阚璞后来回忆说。
二、票钞室里显担当,扫盲班中写新名
阚璞参加新四军后,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票钞室,负责税票装订和印章加盖工作。
前文说过,阚璞在家时没有大名,只有小名“小老巴子”。到了部队后当然要有大名,特别是阚璞所从事的给票证加盖印章工作,每笔交割必须签名。但阚璞参军前没上过学,不识字,给自己起名可就犯难了。据阚璞后来回忆说,当时她请大家帮忙起名字,一下子起了十几个名字,她又不知该选哪个了。最后还是时任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专员的郑抱真知道了这件事,帮忙起了“阚璞”这个寓意很好的名字。
名字有了,阚璞非常开心,但还有开心的事,那就是部队将一些不识字的同志组织起来,进行文化教育。阚璞也被选中参加扫盲班学习。
“记得扫盲班是在一座破庙里,教员都是部队里有文化的老同志。我在扫盲班里年龄最小,个子最矮,大家都非常照顾我,让我感到非常温暖。”多年后,阚璞还能回忆起参加扫盲班的情形,“扫盲班的学习材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编写的、手工刻字印出来的,有图有字,好读易懂;作业本纸张很粗糙,铅笔也很少,为了练字,我们只好用树枝在地下画,用手指头蘸水写;上课没有课桌板凳,不管职务高低,全部一样打着绑腿坐在地上。”在大家的帮助下,阚璞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这样工作方便多了。
尽管条件艰苦,但阚璞和扫盲班的学员们热情高涨,他们边工作边学习,每个人进步都很快。本来需要半年的扫盲计划,他们四个月全结业了。“在结业大会上,首长发给我们每一位学员一本作业本、一支铅笔和一张结业证书。我把这些东西领回来,放在枕头底下,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。”
阚璞虽然年龄不大,但对工作非常负责。她和战友们一起与日军伪造根据地票钞做斗争,保护根据地经济秩序。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,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破坏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阴谋。他们虽然不是战斗在最前线,但也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,他们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这从她的回忆文字中也能看出。
“抗日战争后期,每逢农村丰收季节,日本鬼子便四处掠夺‘扫荡’。为反‘扫荡’,我们会带领老百姓转移。我们非战斗人员也发武器,男同志每人长枪一支,子弹10发,女同志每人两颗手榴弹。这两颗手榴弹准备一颗炸敌人,一颗留给自己。”阚璞说那时候她和战友们什么都不怕,有时和部队一起转移,乡亲们会帮他们化装,借便衣给他们穿,有时还帮他们把脸涂点锅灰,让外人看不出来他们是新四军战士。
当然,阚璞和战友们也时常帮助根据地乡亲们。日伪军来“扫荡”时,会将田里的庄稼抢走或放火烧掉,把乡亲们房子都烧掉。反“扫荡”结束后,阚璞和战友们回到根据地,首先抢收田里烧剩的庄稼,再帮乡亲们盖房。等乡亲们住下以后,部队才修建自己的营地。因此,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,乡亲们十分愿意支援新四军打鬼子。
三、隐蔽战线传情报,红色血脉永流传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。消息传来,阚璞所在的部队以及整个根据地都沸腾了。“记得那一天,我们部队在藕塘镇南边大沙河召开庆祝大会。会场上锣鼓喧天、人山人海,附近部队和老百姓都赶来了。不论军人和老百姓,个个喜笑颜开,整个会场非常热闹。我们在白床单上用毛笔写上‘胜利了’几个大字,用竹竿撑起来去游行,好多人看见了都向我们鼓掌欢呼……”阚璞在回忆文字中说,那段时间,他们喊哑了嗓子,拍红了手掌。
1945年10月,阚璞随部队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天长县。阚璞在仁和集古井寺区政府工作,负责文件收发和来人接待等工作。1946年秋部队北撤,考虑孩子太小,阚璞夫妇决定转移到其他地方暂时隐蔽,后辗转回到老家肥东。1948年春,阚璞夫妇参加了肥东武工队,他们家成了武工队联络点,阚璞担任武工队地下交通员。
据党史记载,这段时间,阚璞经常帮武工队藏、运枪支弹药或送情报等。有一次,阚璞把武工队藏在他们家的两支驳壳枪,放在打猪草的篮子下面,准备送到武工队隐蔽的村子,结果遇上保安团检查。正当阚璞束手无策时,认出保安团里有一名远房亲戚,于是马上招呼他。他一看是阚璞,心领神会地主动来检查她的东西,随便翻翻就放行了。阚璞一看这远房亲戚有争取过来的希望,就向组织进行了汇报。在阚璞的努力下,这名远房亲戚后来果然携枪投诚,还参加了渡江战役。
新中国成立后,阚璞先后在合肥蛋品厂、百货站工作。离休后直至90多岁,老人家依然积极参加多场宣讲活动,宣传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。
从票钞室的灯光到隐蔽战线的风雨,从青春年华到白发暮年……阚璞的成长历程,是无数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的缩影。她的故事,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,更是一盏精神明灯,提醒我们红色基因永不褪色,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(崔建军 程堂义 鲍雷)